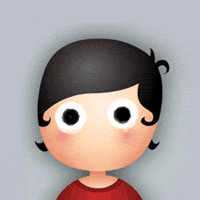多少青春不再,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 \/ 回忆我的舞台生涯
这是第207片树叶儿
1
这个题目很显然有点唬人,我哪里登过什么像样的舞台啊,只不过是误打误撞参加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表演。
类似的演出,在你我的成长岁月中,谁还没有参加过几回呢?
第一次登台表演,你差不多早已经忘记了吧?
2
我到底是如何成长为一个文艺积极分子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事实是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再到中专,直到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我基本没有间断地参加过,除了舞蹈以外的各种演出。
我的这一张黑脸上,曾经一次次地涂抹上胭脂口红,为我化妆的老师一边潦草地帮我打粉底,一边叽咕:
怎么这么黑呀,这得要多少粉啊!
如你所知,我的整个学生生涯中,各种文艺表演的奖状(团体奖和鼓励奖居多),是我唯一引以为自豪的成果,它们同时也成为我不专心读书的一个铁打的证据。
我的父亲在盛怒中不会忘记,把我拎到那些花花绿绿的,贴在墙上的奖状面前,厉声质问我:
你说你以后能干什么?就去做个戏子?卖唱还是翻跟头?
我嘴上不说,心里很不服气:
做戏子就做戏子呗,报纸电视上那是叫人民的艺术家!
3
学生时代的演出,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基本属于那种路人甲路人乙。
我扮演过无数只青蛙中的一只,套着纸糊的绿色的头套,我担心家长不能一眼认出我来;
找妈妈的一群蝌蚪中,我是最小的那一颗,我的任务就是假装不停地哭;
我站在大合唱队伍最后一排的最边上,努力地发挥着近乎是道具的作用;
小话剧里我是弯腰作揖的随从小兵跟屁虫,跟在趾高气扬的鬼子司令的屁股后头;
好不容易等来的古装小品,我是书生身旁的小书僮,佯装挑着笨重的担子,没有一句台词。
最揪心的一次记忆,是有一年参加大合唱,前排的领唱竟然忘记戴红领巾,老师毫不犹豫的把我的给他系上了。
我委屈地躲在最后,从头到尾赌气没有出声,散场时我旁边的同学向老师报告,我一句也没有唱,光是在哭,害得他老是唱跑了调。。
我不记得老师看我的眼神里,有没有些许歉意;
我就记得当时的心情,就像过年穿着一身崭新的滑雪衫,兴冲冲跑出门,转身就被掼炮炸开了一个大糊疤,露出衣服里头的丝棉和布条。
4
要是把我生活过的地方,比作现在的演艺圈,当时的我就有点像如今的三流小角色,不断地露脸混成了薰烧摊上的猪头——熟脸子;
又不能红,始终游走在过气淘汰的边缘。
我靠着一股对文艺的热爱和不要脸就不要脸死不要脸的精神,顽强地乐此不疲地踊跃报名,活跃在各种活动上。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古老而又新鲜的相声了。
我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也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位伯乐,意外地发掘了我的说相声的潜质,由此又挖掘出我的模仿才能,顺带发现我居然还是能唱几句的。
那时候我动不动就在节目里加一段越剧《女驸马》,或是黄梅戏《天仙配》,偶尔还会插上几句老淮调《珍珠塔》,弄得我的母亲很惊讶,她想不明白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学会的。
为救李郎离家园...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哎呀,道一声我的姑母娘啊...
时至今日,这些著名的唱段,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张口就来的小唱段,加深了我的奶奶对我的疼爱。
至于我的母亲,直到我也进入氾水布厂后,在一次职工文艺汇演上,我跟她合作表演了对唱《两地书,母子情》,一鸣惊人,全场喝彩,她才开始认可她这个儿子还是有些本事的。
5
那几年里,乡里的厂里的学校的,甚至一些单位的节庆活动,常常有人邀请我去说一段。
最辉煌的经历就是我和搭档周行老师,通过层层选拨,最终代表扬州市税务系统参加了全省的群众文艺调演。
再有就是我们宝应的第一届电视春晚的10个节目中,有我和周老师表演的相声节目。为此我们在安宜饭店排练了十天时间,荷藕的普通话读音让我痛苦不堪。
那一年春节,我故意不断地跑上街玩,下雪也溜出来,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乡亲看见我说:哎呀,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不丑不丑!
我对天气一向是没有什么怨言的,但是那些天一直下雨,是我比较恼火的事情。
好在正月半过后,电视台又反复重播了。
人在年轻时候的虚荣心,是真的会大到不知羞耻的地步的。
6
我回顾了一下,我前后登过的舞台有:
大小学校和不同乡镇里的礼堂剧院,文化站的小演出厅和溜冰场,乡村的打谷场大队部田埂桥头,企业的会议室大饭堂,街道的敬老院,,宝淮影剧院,大众电影院,邮电局的综合厅,干招会招的多功能大厅大会议室...
为数不多的出县的几次经历这里就不谈了。
哎呀,你看看,我要是一直坚持下来,有关部门不推选我当文艺典型,恐怕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答应的吧。
这些舞台很多已经没有了,保留着的也基本面目全非了,但是他们在我的记忆深处依然完好如初。
套用一句老话来说,我在那些舞台上挥洒过汗水,也滴落过泪水,收获过喜悦,也饱尝了挫败。
7
第一次在氾水电影院里说相声,是那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和搭档布厂前织车间的张姓同事都特别紧张,他是说话抖,我是两条腿抖。
我在相声里模仿了朱明瑛唱《回娘家》,头上的方巾老是滑下来,慌乱中打了个死结,唱完了又解不下来了。
后来在宝淮剧场演出时,说了一大半,台下愣是一个不肯笑,还有观众大声地嘘我下去呗,我又急又羞,满头浑身的大汗,恍惚之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只是觉得嘴皮子发麻,干燥得要命。
舞台上的射灯几乎刺瞎了眼睛,我慌里慌张地逃到后台,跑到后院的厕所里面忍不住地伤心地哭。
当时的领队文化馆的王长春馆长居然找到我,拍拍我的肩膀用他的南京话安慰我说:
没得事,很正常好吧,好多大艺术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嘛。
那一年去射阳湖乡巡演,我嗓子有点哑。等到快要上台了,一起的一位唱淮剧留着齐耳短发的小姐姐,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塞给我两盒草珊瑚含片,嘱咐我不要紧张,好好说,肯定行的。其实我们一直都没说过话。
巡演结束后直到今天我也没再见过她,我甚至都忘记了她的名字和长相。
8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两次经历。
一次是那年录电视晚会,突然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有人小声说,县里的干部来审看节目了。
平时打打闹闹惯了的演员们突然都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在无声地走动忙碌。
领导们齐刷刷地坐满了前三排,边上的导演喊预备——开始!
领导们面带笑容,频频鼓掌,对着空无一人的舞台。
后来正式播放时,我惊讶地看到镜头的巧妙切换穿插,给人的错觉是领导们从头看到了尾,认真投入地颔首微笑,从容优雅地拍手致意。
其实当时就录了20分钟不到,录完他们又前呼后拥地撤离了演播厅。
电视台没有播放的,就是现场有人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全体演员的不尊重,小声地发牢骚说:
这时候要是来个特务,扔颗炸弹保管一锅端。
还有一次就是在南京,我一直没能搞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这位领导身材魁梧大脸盘很严肃,比我还要黑,又没化妆搽粉。
他倒是看完了整台节目,问题是从头到尾板着个脸,压根就没蹦出一个字来,弄得全场特别压抑,连呼吸都感到沉闷。
我们如同陷落在敌占区,被敌人用枪指着,屈辱而痛苦地演完了节目。
后来看春晚我就特别能体谅那些演员们,就像老歌里唱的:
戏子的痛苦,谁能够明了?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辛酸的泪。
9
那时候我们四处演出,伙食自然是差不了的,运气好了还会分到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都还挺实用的,比如电饭煲,节能灯,微风扇,电热毯,羊绒被,四件套的床上用品……
我的妈妈和奶奶有时候想要添置什么东西了,忍不住地会跟我打听,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演出啊?
不过我最开心的是,能够发些现金补助,我就可以去买些信纸邮票,甚至是喜欢的书籍了。
我是怎么慢慢地远离了舞台的呢?我分析过其中的原因。
一来大家的文艺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可以选择的项目越来越多,我们那样的演出不免显得单调落后了。
二来我当时也来宝应城里上班了,单位的头是不赞成我动不动就被借用出去的。在他看来唱唱跳跳耍嘴皮子总归不是正事,耽误了单位的差事,工资还一分不能扣,不划算,没必要。他高低不准我假了。
当然最关键的可能是我自己越来越不想再掺和那些表演了,觉得自己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收收心忙些所谓的正事啦。
10
可是我一直忘不了那些舞台生涯。
我总是一次一次地怀念那段时光,怀念那些念词背词对词,排练彩排走台,掌声喝彩谢幕。还有那些匆忙里的转场,晚归中的疲倦。
当时结识的好多朋友,我们一直相处至今。
如同提着一盏灯,从当年的舞台上走下来,走过漫长的岁月,那束光芒依旧温暖如往昔。
那段经历宛如一对翅膀,带着我这样一个懵懂的乡村少年,飞到东飞到西,带我去看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去看那形形色色的人们。
甚至可以说,正是那样的一段经历,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和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今天的自己。
那一年我刚刚做了记者,有一次去偏远的夏集镇,采访县里的送文艺下乡活动,临要开始时,主持人不知道怎么没能赶来。
大家正慌神呢,带队下来的王长春馆长,一眼看到坐在前排的我,喜出望外地一串碎步跑过来,把节目单塞进我手里说,赶紧的,救个场!不要啰嗦,走走走!
我发挥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机智和口才,赢得了乡亲们的喝彩,圆满地完成了临时主持人的任务。
结束演出返回的大巴上,皎洁的半轮明月洒下轻柔的光华,我感到无比的愉悦和满足。
我想倘若没有那些年的舞台生涯,我肯定没有底气,。
人生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舞台生涯,真好。
这是命运的丰厚的馈赠。
即或是哪一天我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我依然是个怀揣着满满的回忆的人。
来啊,朋友,说说看,第一次登台表演,你是否还记得那么真切?
2016-9-25
图文无关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