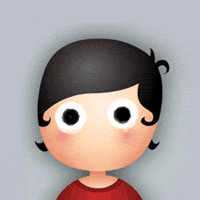过往风流·杨海霞 | 金农:丹青不知老将至
《中国美术报》第52期 美术副刊
多年前,郑板桥这样评价自己的朋友金农:杭州只有金农好。
时间的过滤往往公正不倚。出生在杭州的金农被贴上“扬州八怪”之首的标签,这一标签的意义就是,直到如今,人们依然会认为,金农以神奇的方式,超越了他的时代和文化,他的价值无法低估。一如他毕生有金石之好,这种对永恒的追求,同时铸造了他的书画语言。
金农小像
八怪之中,我尤喜金农。他首先应该是以诗人雄名于世。几年前买到一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的《冬心先生集》,爱不释手。据说还有线装本的《冬心先生集》,看孔夫子旧书网,价格太高,却又极其想收入囊中,这几天辗转反侧,想来就为此事纠结。
金农的画,笔法古朴,拙趣横生,而他的漆书,“金农墨”浑厚如漆,与画相得益彰。我们看他的《杂画册》之《荷塘忆旧图》,就是如此。这是金农的一幅设色点染之作。画面,长廊,栏杆,荷叶清丽,一人凭栏赏荷。倒也是寻常景致,深深浅浅随意点染的绿便是那荷,并无技法精深之感。右上角题为:“荷花开了,银塘悄悄。新凉早,碧翅蜻蜓多少?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
【清】金农 荷塘忆旧图
清人方薰《山静居论画》云:“画有可不款题者,惟冬心画不可无题,新辞隽语,妙有风裁。”金农则自言,“每画毕,必有题记,一触之感。”读者无法不被金农浑然天成、耐人寻味的题识触动,又被这沉厚古穆的书法所吸引。纤手剥莲蓬,手有余香。荷塘清香四溢,静默不言。同坐的“那人”是谁?而今“那人”又在哪?夏荷之清香,阵阵袭来。“那人”寻遍画面不见,却又无处不在。你看着这花开了,这花又败了,世间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你也无法一一去细说,然而此时说不定就在这荷塘边,你正与“那人”相逢。
此画作于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此时金农已有73岁。
这一年,他自写小像,一飘然长须的老者,沉然前行。他以焦墨渴笔勾勒自己形象,漆书题款,曰:“予今年七十三矣,顾影多翛然之思,因亦写寿道士小像于尺幅中。笔意疏简,勿饰丹青,枯藤一杖,不失白头老夫古态也。”他也曾“家有田几棱,屋数区,在钱塘江上,中为书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无穷”,却终身布衣,五十岁以后才学画,老年时生活困窘,寓居扬州西方寺,靠抄经刻砚度日。1763年,金农77岁,殁于扬州佛舍。次年,由友人、弟子筹资归葬杭州。
与刚到扬州的落魄相比,金农也有“岁得千金”之时,但他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工书善画,好鉴藏,加之传统文人品格的束缚,“千金之财”也只能“随手散去”。
我倒以为这是金农乐意的归宿,不被世间财物所累,也不求闻达,一室之外,不过山水而已。
何况,金农还有两个最为得意的弟子,罗聘和项均,对他来说,也是圆满。后世也有许多金农的追随者。微博上有个叫老树画画,他的画面很简洁,不过是长衫、春光、山村、田园之类,人生智慧却也非常独特。每次看到老树的画,我总会想到金农。但是,看到老树的一个访谈,他正色说:我没有临摹过金农。
好吧。这位时常能创作出“非复尘世所见,盖皆意为之”的画作的金农,涉笔即古,脱尽画家之习,却又现代感极强。他宜古宜今,并不孤独。
《昔年曾见》,女子青衣素钗,清简素妍,神情安详,怀里抱着婴儿,静静地坐在树下。树冠上是一簇簇的朱红色叶子。她的眼前是淡青色的远山。右上题款“昔年曾见”,有着无尽意味。小字款云:“金老丁晚年自号也”。钤“金老丁”印。有说此图为金农在古稀之年所绘,寄托了对亡妻和早夭小女的怀念。
【清】金农 昔年曾见
昔年所见,不只是回望,也不仅仅是眷恋,更多的是对当下以及未来可安顿精神之处的寻觅,那是更宽广,更为豁达的所在。而人的存在,会使画面展现的不仅是一个空间,还是一个时间停止的瞬间。
金农在绘画里加入如此多的文化因素,而不是追求本体绘画。在他的作品中,时常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时间感,同时也有很强的哲学意识。有人称其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个文人画家”,并不夸张。
我们看到了《荷塘忆旧图》中并未出现却又无处不在的纤手剥莲蓬的“那人”,看到了《昔年曾见》中若有所思的女子……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想起浮士德的呼唤:“请停留一下!”请停留一下。回望过去,还有如此旖旎的情绪。内质风雅,沉静如水,不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哀伤。画家以或浓或淡的朱青勾勒,或深厚饱满或清淡苍茫,都已在丹青不渝中潜入读画人的心中。而你也会惊觉自己许多细微的情绪,正被他叙述。那种感觉,就如那日我走在绿荫蔽日的南山路,突然听到肖邦G小调叙事曲,这种平静而又惊艳的渗透。
金农30岁时始用“冬心”为号,取自唐崔国辅《子夜冬歌》中“寂寥抱冬心”之“冬心”。金农善画马、画竹、画佛像,尤喜画冬日之物,譬如,梅花。
我也爱梅。住的地方有个小院,前后都种了梅花,有婆娑的白梅、朱砂梅……有一日看一个画家的绿萼梅,雅致得不行,于是再补了绿萼梅种上。
【清】金农 梅花
吴昌硕自号“苦铁道人梅知己”,每每看他的梅花,我就很想在立春前后的时候去余杭塘栖的超山探梅,那是郁达夫笔下的超山的梅花:“梅干极粗极大,枝叉离披四散,……故而开的时候,香气远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麓,登高而远望下来,自然自成一个雪海。”但是,终归觉得吴昌硕的梅花太气势捭阖,疏阔纵放。说起来,我还是喜欢金农的梅花,不疏不繁,松紧自如,在萧瑟冬日,有春风浩荡之姿。
“扬州八怪”中,不止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也擅长画梅。据说李方膺画梅尤精,有印章曰“梅花手段”。汪士慎老年失一目,却挥写自如,自称“尚留一目看梅花”。金农之梅冷艳,或无数花枝颠倒开,或枝繁花繁地成长,或横枝疏影,或冻萼一枝,长在溪边,长在原野上,长在庭院中。它们是“水边林下两三株”,或是“驿路梅花影倒垂”,或是在“客窗偶见绯梅半树”,还有“吾家有耻春亭,亭左右前后种老梅三十本”等等。这些梅,总有清气,冷香裹在寒气里,有时以千花万蕊夹之,有时一枝梅花,影影绰绰的花朵,有时千枝万朵,占尽风雅,而点蕊时笔端有力,风神俱足,似乎将毕生心力一并融入画面,又有漆书题在一边,你不着迷都不行。
迷金农梅花的人很多。张大千最后的一个生日,台静农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多打了圈圈,张大千视为珍宝,竟说:“这是冬心啊。”记得董桥有写道:“四十多年前沈茵的舅舅收进大风堂旧藏金农墨梅一幅,画好诗好,还有张大千藏印,标价贵,买不起,错过了。”又有一处,“金冬心的梅花其实更可喜,一圈一圈圈出清白乾坤,听说代笔多,假的多,我不敢要。”董桥对金农的作品是心心念,他说自己金冬心的真迹买不起了,只好看看李智刀下刻的金农让自己心中舒服下。
就是这样,金农的梅花,在初春,在深冬,一朵两朵梅,一束梅花,或者一树梅,或者万枝梅,突然会花光迷离,让人将六朝山水弃之一边。
冬心是单纯的,有时甚至是寂寥的,他用笔简单,圈圈点点,不疏不繁,全是文人画的微妙之处。
在密萼繁枝之中,或者在寂寥的一树梅穿过篱笆而来时,看似漫不经心,却笔简意远、片片含情……
我早已奢望自己是金农笔下的一朵梅花(岂敢有一树之妄想啊),被他的笔轻轻润过,那一刻,想必就是他所指的“晚香冷艳尚在我毫端也”。
丹青不知老将至。无论何时,读金农,他都不老。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
□曹宗国
为什么人们把清代中期活跃在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称为“扬州八怪”?权威的解释说是由于他们的艺术风格被正统画派视为不入流,这种解释其实是有意模糊和掩盖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扬州八怪”就是一群不合时宜的文化精英,他们远离庙堂官场,退居民间江湖,用故意搞怪的书画来愤世嫉俗、秉持清高,于是世人就用“扬州八怪”来赞许他们的为人和艺术。
首先,从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来看,“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都是些看透封建官场内幕,要么终生不仕,要么仕而退隐的读书人。比如最有名的郑燮(郑板桥),他本来在康熙年间曾经应试科举为秀才,雍正十年为举人,乾隆元年为进士,在山东范县、潍县当了知县,可是因为在遭遇大饥荒的年头请求救济饥民,态度、措辞激越,得罪了朝廷大官僚,于是托病辞官,归于江湖。
又如李鱓,他于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但被排挤出来。乾隆三年又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也是因为得罪了上司,在两革科名一再贬官之后,心灰意冷,从此到扬州卖画为生。
还有一个李方膺,本来是“官二代”,还当过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而且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却因为被人诬告而罢官,他愤而退隐南京,在借园当了寓公。
除此之外,另外几位更是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终身不仕。如高翔,终身一介布衣;金农一辈子未做官,虽曾被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却未试而返;黄慎自号“东海布衣”,家境困难,宁愿寄居寺庙也不去求一官半职;而罗聘则更是以江湖野老自居,自称“花之寺僧”“金牛山人” “洲渔父”,以示不与士大夫同流合污。
这样的社会经历和身份地位表明,“扬州八怪”都是些有着强烈正义感和高尚志趣的文化人。他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逢迎拍马等作风深恶痛绝,决心不与之为伍。他们才华出众,有着敏锐洞察力和社会良知,同情民间疾苦,于是就将自己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融汇在诗文书画之中,并借以抨击丑恶的事物和人,表达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统主流的独创“怪异”的艺术风格。
比如郑板桥的书画就是如此。他把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有的“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有的则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也传达出他的思想情感和志趣。他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这种字体的意趣和精神是什么,从至今广为传世的“难得糊涂”那幅字里,人们完全可以体味出来。郑板桥公然宣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一语道破了他的思想和艺术之所以“怪”的奥秘。
还有那个爱画鬼的罗聘,他笔下的鬼形形色色,但共同点是“遇富贵者,则循墙蛇行,遇贫贱者,则拊膺蹑足,揶揄百端”,而且“凡有人处皆有鬼”。你看,他哪是在画鬼,分明是在揭露那些趋炎附势、欺压贫民的污吏。他的《鬼趣图》就是描画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讽刺当时的世态人情,无怪乎当时的一些权贵官僚,看了他的画都摇头直称“怪哉、怪哉”。
“扬州八怪”都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和精神追求。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确实,作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人,“扬州八怪”之怪, 正是他们傲世独立的高尚人格和艺术风骨之所在。
意犹未尽?
更多内容 点击可直接阅读:
◆弘扬中国美术精神 彰显中国美术气派
◆关注美术前沿热点 报道中外美术新闻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国家画院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92
国内邮发代号:1-171
海外发行代号:C9257 官方微信:izgmsb
►联系我们:zgmsb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