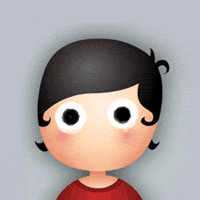雅萍讲故事:讲个故事给你听 (获奖作品选登 经典重温)
李亚萍(播名雅萍),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诗歌朗诵美文欣赏节目《新疆好声音》主持人,播音指导(正高职称),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新疆首届广播朗诵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从事播音主持工作20余年,数十篇播音、主持、专题、新闻类作品获全国和新疆广播电视播音及新闻类作品一、二、三等奖。
雅萍讲故事:讲个故事给你听
听读悦赏│《青衣》雅萍播音主持获奖作品
(江苏) 毕飞宇 @ 文 (乌鲁木齐) 雅萍 @ 播音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韵的极少。 筱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
二十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二十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
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筱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筱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四十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 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采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筱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
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她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簧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
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筱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筱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从筱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著和期盼。
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毕飞宇,男,1964年1月生,江苏兴化人。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职 业 作家、教授 毕业院校扬州师范学院
主要成就 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大红鹰奖
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人民文学奖
代表作品 《那个男孩是我》《青衣》《平原》《慌乱的指头》《推拿》。
作品鉴赏
《青衣》横亘千古的女性悲歌
主题思想
“青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戏剧行当,出一个好青衣是千难万难的事情。“十九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冥冥之间,筱燕秋与“青衣”有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奔月的嫦娥则是一个标准的“青衣”角色,她是后羿的妻子,但由于射日英雄的光芒是如此璀璨,以至于迫使她仅成为与快刀宝马等价的英雄身边的点缀,而完全掩盖和抹杀了一个美貌鲜活女子应该拥有的千般妩媚、万种风情。为了摆脱这种物化的附庸关系,为了从男性森严统治的缝隙中透漏出自己的光芒,获得自身的独立,嫦娥毅然选择了悲壮地孤身离去。她完美地体现了一个“青衣”应该具有的风骨与神韵:哀婉、幽怨、缠绵悱恻又风情万种,代表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生存境界。筱燕秋迷恋“青衣”表演、陶醉于舞台上与嫦娥一起飞升、如梦似幻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实现女性自由生存最艺术化的手段。于是,嫦娥、“青衣”、筱燕秋,这些处于不同时代却预示着女性相似命运的意象和人物纠结在一起,演绎了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在20年前曾红极一时:她在舞台上眼波流转、顾盼生姿,是令人艳羡的青衣新秀,众星捧月的大牌和台柱,前程似锦。然而,戏演完了,帷幕落下之后,孤独和凄清便来了,平凡和世俗也来了。她没有羽化登仙,没有飞升离去,更没有在广寒宫里轻舒广袖、浏览人间春色。她仍然是一个生活在真实人间的平常女人。这“真实”发展到后来甚至是残酷的:她的老师李雪芬将嫦娥塑造得巾帼豪杰般铁骨铮铮,这无异于玷污了筱燕秋心目中真正的嫦娥。为了捍卫自己的艺术信仰,她把开水浇在了李雪芬脸上。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她离开了舞台,也离开了她钟爱的“青衣”与“嫦娥”。从此,筱燕秋便开始了血泪班驳的自赎之路。
被俯视的女性存在困境
筱燕秋表演“嫦娥奔月”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其中两次都与男性相关。1958年,在献礼共和国十周岁生日的《奔月》公演前夕,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愤然表示,“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是理所当然的时代“伟人”,它以不容置辩的姿态宣布了《奔月》演出的半途夭折。有趣的是,20年后,烟厂老板又一手促成了《奔月》演出的起死回生,这不能不让人叹服历史变迁那翻云覆雨的能力。只是,,这时的“伟人”已由将军一变为腰缠万贯的老板,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果战争爆发,他也许就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家,一句话,他是个伟人”。在揶揄意味浓烈的语气下隐含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哪个时代,女性总要处于这些“伟人”般男性的俯视之下,她们注定无处可逃。毕飞宇说,“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对于女性而言,这些高高在上的“伟人”就是那个“鬼”,在这个“鬼”的俯视之下,女性存在的困境愈显狰狞。烟厂老板在20年前曾暗恋舞台上大红大紫的筱燕秋,把她当女神一样供奉在心里。
20年后,因握有经济大权,上天给了他重续旧梦的机会,他终于可以将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还原为实实在在的凡人,并玩弄于股掌之间。与其说他觊觎的是筱燕秋的美貌,不如说他要征服舞台上那个曾经桀骜难驯的嫦娥。他要把曾在嫦娥那里丢失的男性权威抢夺回来。因此,烟厂老板在对筱燕秋肉体的征服中,得到的不是猎艳后的肉体欢娱,而是重获男性权威的快感。这时的筱燕秋“认定了今晚是被人嫖了。被嫖的却又不是身体。到底是什么被嫖了,筱燕秋实在又说不出来”。正是这“说不出来”的东西满足了烟厂老板的征服欲。它表明:经济上的强力可以无限扩张,延伸到生活的任意领域———甚至包括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占有与征服。它撕碎了蒙在温情世界上最后一层薄莎,将最惨烈的真相呈现出来,女性生存的困境就在这里。除却“伟人”般的男性,与筱燕秋息息相关的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是丈夫面瓜,一个是剧团团长乔炳璋。由于筱燕秋的“青衣”情结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迷恋,它排斥一切与此情结无关的人与事,所以“表演自恋这幕喜剧只能以牺牲现实为代价,想象中的角色要有想象中的观众来崇拜。一个迷恋于自我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控制,她不关心与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面瓜与筱燕秋的婚姻因为后者的极端顾我而显得虚无飘渺,面瓜则因无法真正走入筱燕秋的精神世界而变得无足轻重。乔炳璋的处境与面瓜一样,作为无力掌控时代走向的边缘人,他们是“去势”的男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与筱燕秋一样,都处于“伟人”权力话语的俯视下,共同感受着生存的困惑与艰难。
“药”———女性身体的秘密
在美好的传说中,嫦娥因一颗灵药而脱离肉身飞升得救,然而历史和现实却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生存提供任何一剂灵丹妙药,凡人也终究无法逃离沉重的肉体凡胎而飘然成仙。更令人气馁是,千古而下,女性不仅没有获得超脱的能力,反而承接了自“嫦娥”就开始与“药”结下的不解之缘。患有身体或精神上的病痛,不是受到了外在与内里的伤害的人才服药。如果不于是,“药”成为一种隐喻,它有效地指涉着女性身体和这身体所隐藏的一切秘密,揭示了她们长久以来被损害被侮辱的悲剧宿命。
《青衣》主人公筱燕秋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身体规训。在告别舞台20年后,为了留驻青春,重返舞台,筱燕秋开始对身体进行自觉、不自觉的塑造。她首先从医院拿回大包小包、形色各异的减肥药,希望借助药物可以让时光倒转。然而,面对无情的时间之流对女性的摧折,她又不得不接受青春年华一去不返的现实,“说到底时光对女人太残酷,对女人心太硬,手太恨”“时光的流逝真的象水往低处流,无论你怎样努力,它都会把覆水难收的残败局面呈现给你。让你竭尽全力地拽住牛的尾巴,再缓缓地被牛拖下水去”。一具臃肿陈旧的肉体承载不了高飞的灵魂,筱燕秋与春来在排练厅中度过的那个难于启齿的下午就是她对过去时光的精神反刍。她抚摸着春来年轻的身体就像触摸到20年前的自己。她对春来的喜爱与依恋就是对年轻自己的追怀与哀悼。接着,筱燕秋终于等来了舞台表演的时刻,但这一刻的获得却以牺牲腹中生命为代价。因为一次偶然的性欲放纵使筱燕秋珠胎暗结,性成为对筱燕秋这一女性身体进行规训的权力之一。福柯认为,“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和最内存的要素”。面对烟厂老板,筱燕秋为了实现青衣表演之梦刻意奉迎;面对丈夫,她表现出难得一见的热情,性似乎成为女性追求理想与表达情感的有效手段。直到后来,因担心怀孕影响表演,筱燕秋果断做了人流,性的权力机制才真正浮出水面。受孕这一独特身体质素使女性区别于男性,也成为女性备受折磨的来由。而堕胎无疑是对女性身体最惨痛的折磨,在青衣表演与堕胎之间,筱燕秋别无选择,在男权网罗的覆盖之下,女性更是无从选择。
“黑色窟窿”———女性虚妄的救赎
筱燕秋一生执迷于青衣表演,当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她不能不陷入疯狂,“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唱的依旧是二簧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筱燕秋旁若无人,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雪地上,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这些触目惊心的“黑色窟窿”就像女性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无望挣扎,丑陋而空洞。《青衣》除塑造了悲剧主人公筱燕秋之外还设计了另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李雪芬和春来。如果说20年前的李雪芬是一个永远也没有希望飞升的嫦娥,那么20年后的春来却是一个独具风韵的“青衣”。“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一个风月无边的女人,一个你看她一眼就让你百结愁肠的女人”。遗憾的是春来追求的不是嫦娥的飞升,也不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她需要的仅仅是切实的现世利益。李雪芬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扮演了一个代表着刚强、勇敢时代精神的嫦娥,春来则是商品经济大潮洗礼下的新一代青衣。她耍手腕,用青春的活力与美丽同烟厂老板做交易以换得登台演出机会。她将“青衣”要坚守的艺术精髓置换成金钱社会应遵守的等价交换原则。经济社会的生存准则最终战胜了崇高的艺术信仰。
其实,无论是李雪芬还是春来,她们同筱燕秋一样都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承载者。不同的是,筱燕秋不甘臣服,不接受历史赋予的性别角色,反抗的表现便是对“青衣”的钟爱和对嫦娥的迷恋。可悲的是她的抗争失败了,最终还是落入了生活和命运的圈套。李雪芬和春来则自觉认同了外在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她们不仅以男性的审美眼光塑造自己,以父权制的规范约束自己,还以此去压抑其他女性。波伏娃认为,“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当外在压力被内化为女性自身的精神准则时,她们不战而败的结局便命中注定了。如果“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是嫦娥的一种生存状态,她的寂寞孤独是因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李雪芬和春来所面对的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尘世的纷扰和污浊。而筱燕秋却是一个在半空中沉浮不定的女人,她的失重搀杂了更多的痛苦和无奈。也惟其如此,筱燕秋的失败和自赎才更加悲壮和耐人寻味。
艺术手法
视角转移
在《青衣》的整部作品里,叙述者的语言风格一直是有些调侃的,有意与小说情节和作品中人物拉开了距离的。但是一旦叙述者的视角在局部转移为主人公的视角,语言风格就变成了一种带有诗意色彩的主观性语言,带有很强的感染力。两种语言风格的反差在文本中形成一种内在的对话,更加突出了聚焦人物的性格特征。
同时,虽然第三人称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他有权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但叙述者从自己视角看到的人物内心与人物自己在叙述中表现的内心情感带给读者的感情认同度是不同的。如筱燕秋对青衣这一角色的个人看法,小说用了长长的一段对其进行描述。段落一开始就用她对旧时艺人的反驳作为从叙述者向焦点人物视角转移的标识:“筱燕秋从一开始就不能同意这句话。那怕你是一个七尺须眉,只要你投了青衣的胎,你的骨头就再也不能是泥捏的,只能是水做的,飘到任何一码头你都是一朵雨做的云。这样的话是诗意而个性的,只能是从筱燕秋的嘴里才能听到的。筱燕秋的不谙世故、痴迷入戏只有通过筱燕秋自己的视角才能更好地表达出来并得到读者更充分地认同。再来看。《青衣》是如何通过叙述视角由叙述者向其他人转移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当人们提起因为两位青衣争演嫦娥而导致《奔月》下马的往事时,老艺人所谓,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筱燕秋做那样的事疑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眼光下的道德评价。
事实上,在对于筱燕秋年轻时主演《奔月》的风波的描述中,叙述者的评价似乎也是和这种公共眼光合流的。毁掉燕秋的前程就是一句带有道德评价意味的对一段往事的引导语。这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悬念,想知道这一风波中的焦点人物的真实想法,是不是跟公共眼光的评价一致,以下的叙述视角从叙述者转移到焦点人物时,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格外关注。同时,随着故事的渐次展开,读者会了解到筱燕秋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单纯的嫉妒,而是由她不同凡俗的个性所致。这样,读者对焦点人物的评价与其他人物甚至叙述者的部分态度就产生了差距,作品也由此而获得了一种文本之外的张力。
叙事结构
《青衣》的故事性较强,采用比较传统的外结构叙事当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无论是用倒叙在文本开头引入过去,还是在中间用插叙使过去、现在两相对照,作品都是在线性因果的结构中展开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外结构。之下隐藏着很强的内结构因素。首先,筱燕秋的过去和现在虽然同属一个序列,但它们的重复性和重复背后蕴含的不同意味,这些却有着潜在的为揭示命题服务的作用。简单地看,筱燕秋似乎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和同样的悲剧,但是如果细加体会,读者就会发现不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筱燕秋对于嫦娥这一角色的执著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种执著受挫的原因。年轻时的筱燕秋无法容忍一点点对于嫦娥这一角色的不正确理解。另一青衣名角李雪芬因扮演《杜鹃山》的柯湘而成名,筱燕秋无法容忍她用演绎柯湘的高亢的嗓音和奔放的激情来同样处理嫦娥这一角色,这种旁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在筱燕秋看来却无异于对角色的一种亵渎。基于此,筱燕秋才会对李雪芬冷言相加乃至动手伤人。这是筱燕秋对于艺术执著的必然表现,也是她不懂人情世故的表现,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筱燕秋最终却不得不向李雪芬道歉。由此可以看出,筱燕秋在此时的痛苦源于她在世俗世界和艺术世界的分裂。
而在《奔月》。的现在的排练和演出中,筱燕秋对于艺术的执著已经使她在艺术世界里也不得不痛苦地分裂。一方面,面对因韶华已逝而远不如前的身体和嗓音,她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年轻学生春来推上前台;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抑制自己几乎是用生命对嫦娥这一角色的热爱。这时,筱燕秋的悲剧就具有了用艺术同时间相抗衡的形而上学的悲剧意味。正是这两方面、两时期内涵不尽相同的悲剧共同组成了筱燕秋执著艺术的悲剧故事。另外,在《青衣》,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潜在的内结构因素,那就是剧中之剧《奔月》,这是故事之所以发生和展开的核心。虽然由于(嫦娥奔月)的故事一般的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作品无从也不必赋予这出剧中之剧以结构上的特殊意义而予以展开(如果是那样的话,这种潜在的内结构因素就成为显然的内结构叙述了)。但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自然会把嫦娥在月宫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寂寞同筱燕秋因执著于角色而形成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寂寞联系起来,由此,《奔月》这个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意象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的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这个隐喻不仅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而且使小说在不动声色之中获得了诗意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