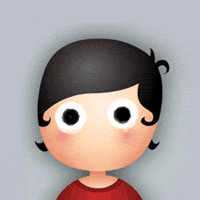关于自行车维修的哲学探讨
自从张对对离开后,我总是想把我俩之间的故事写在纸上,却总是在开头便夭折。我试过套用呼啸山庄的开头:
2017年。我刚刚看望过张对对回来——就是那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张对对。
也许因为张对对并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希斯克利夫,于是这个开头对于被我强行安放在我们的故事之前这件事很是恼火,因此我接下来在电脑上写下的一切都越来越像是一个无趣的市井笑话。在无数次不死心后我便彻底放弃了这件不可能的事。她那么来去自由的一个人,肯定不会喜欢我把她写在我的故事里,即某种程度上的将她给束缚。
我出了酒吧,在路边一个超市买过烟之后,便走进了地铁站,然后便看见张对对瘫坐在扶梯上,头倚在一侧,随着扶梯的下降而规律的晃动着脑袋,丝毫不在意马上就要到底的扶梯。只是可怜的我从小就接受着见义勇为的教育,于是在她将要亲吻地面的时候抓住她的衣领,吃力的把她拉了起来。她却灵活的像个猴子,借力使力,一拉一扯之间,一个柔软的满是酒气的身体便扑在我的背上,两条胳膊挂在我脖子上一扣就不再分开。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烂醉如泥的女人趴在我耳边大言不惭:“走,我带你回家。” 而我竟顺从的没有任何反驳。而后她便仿佛一睡不醒,对于我的任何询问都没了回答。
于是我背着烂醉的张对对在一号线的某个站台等着一辆可能不会来到的末班车。所有末班车都是不准时的,就像这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的结尾,都有着无数的理由鲜克有终,比如亲人的去世,也比如爱情的消失。
那天的末班车终究是没有来,或者它早已开去,而我迟到了也许也成了不争的事实。至于迟到了一分钟还是半小时便也了无意义。不过张对对直到离去也没有跟我讲起她的体重,我想可能她那天并没有醉到失去意识,对于这个问题她心里也是一直介意着的。
后来,我问过张对对,为什么选择对我这样一个众人眼里的失败者死心塌地。她的答案一如既往地简单。她说,因为她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是在长椅前面的地上睡得像个死猪的我,而不是在我家的床上一丝不挂的我。我心里苦笑,毕竟那天是传说中的情人节,我又何德何能能在众多情侣翻云覆雨的时刻寻得一间空房。于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应该对那列不准时的地铁抱以感谢:如果我赶上了那列地铁,也许我就有力气把她背上我十楼的家,也许她也就不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赖在我家并且霸占我那张小床的四分之三。
虽然我从不允许她在床上抽烟,因为那样会让床单枕头都沾上很重的烟味,我讨厌烟味即便我也抽烟,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她抽烟的样子很好看。好看到以至于每当她燃起香烟,我总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的看着,看她优雅的捏着烟,看她的唇微张亲吻滤嘴,看着直到她从口中不紧不慢的吐出那些云雾缭绕。
那张被她殖民的小床又破又旧并且形状奇怪,一翻身总会吱嘎吱嘎的乱叫,她也爱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家的床把她该叫的都替她叫了。于是每次做爱我都担心床会突然间散架,会把我的小和尚扭断。有次我俩躺在床上对视许久,她突然问我说,四目相对是骗人的吧。我看你的眼的时候只能注视着你的左眼或右眼 两个人又怎么才能四目相对呢。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四目相对只存在于两个相爱的斗鸡眼之间的深情注视里,然后我问她可否愿意与我四目相对,她没有回答只是笑着说:“你也是斗鸡眼吗?”
张对对其实是个很哲学的人,她喜欢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剥着床边斑驳的清漆,会纠正我仅仅来自高中政治课本的贫穷的哲学知识。可是毕竟我们仍旧是凡人,长久地高谈阔论着,是会累的。于是话题也总是习惯性的跌落云间,滑向昨天早市上那颗长得像我脑袋的白菜或是那个喋喋不休的发福女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