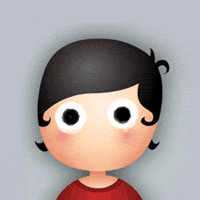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我的推文在写下“姚家埭”三字后,突然停滞了近三个月。这是因为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梳理,一时竟无从写起。幸好,所有的回忆里都是甜蜜,也就不觉得冗沓了。
表姐夫夏志中先生长期在老家镇政府做基层工作,最近他有感于新一轮拆迁大潮下原住民的离散,想收集一些乡野俚语和旧时典故,以示纪念。他来电问我有没有资料可以提供,特别是我的出生地——马山镇渔港村的。我不假思索地表示了歉意,因为实在一下子提供不出有用的东西,同时我又不假思索的推荐他可以多多关注姚家埭村,直觉告诉我,那儿应该比渔港有料的多。真实的原因是:
姚家埭在我心里的印记远胜于我出生和居住的渔港村。
姚家埭小学。我的童年大半是在马鞍度过,1987年春节后,因父亲工作的变迁返回出生地——马山镇渔港村西溇底,进而入读邻村姚家埭小学。小学校的前身是马山区中心校,再往前,据父亲介绍,大约在解放前后,由一位姚姓族长捐出了姚氏宗祠而创立。学校很大很阔,在小孩子眼里,完全是一个玩乐的天堂。大门朝南临河,整个校园布局呈三进,由南自北地势渐高。临河的一进是食堂、教工宿舍及乒乓球室,西侧北折一排附属房是体育器材室。中间的一进有教师办公室和音乐教室。最北一进是教室,西侧一大间是个大礼堂,也是我们雨天活动的处所。一、二进之间是一个天井,一棵老枇杷树上满满留下了我们攀爬的脚印。二、三进之间是个泥操场,教室外走廊台阶下是遍地黄花菜的花圃。西侧附属房和二、三进之间又是一个大泥操场,杂草丛生。最有趣味的是在第三进和北围墙间,这是学校的后园,也是学校地势最高点,需要拾阶而上。东半是菜地,每班都分配有养护任务。西半是一片野树林,我们一下课总会到那里折下树枝盘在头上躲猫猫、打野战。在姚家埭小学宽阔野性的空间里留下了我许多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印记。
1950年前后姚家埭小学简图(父亲手绘于2018年2月)
1987年前后姚家埭小学简图(我绘于2018年4月)
姚家埭小学正门旧址(2018.1.27摄)
姚家埭小学正门河埠踏道(2018.1.27摄)
肉蒸饭。那时路稍远的学生午餐都是自备的。每天一早到校先淘好米将铝饭盒放到学校的蒸架里,中午各自取食,至于下饭菜,就依各家条件各有不同。妈妈隔一两周总会奖励犒劳我一下,为我准备一餐美味,那就是:肉蒸饭,我把它叫作:饭蒸肉。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蒸饭的铝盒中,将3、4块生鲜猪肉与糯米一起放好蒸,撒点盐,再讨点酱油来,就是豪华午餐了。米必须是糯米,有粘性,蒸熟后用筷子一挑,饱满的饭粒带着汁浆缓慢散开,我戏称它会“爬”。肉最好是五花肉,夹精夹肥,油而不腻。这样的午餐,有饭有肉,粘润鲜美,可称大美。要知道,87、88那几年,物质紧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我也算是一个小开了。
“漏”。小学校年久失修,一遇大雨,瓦顶经常漏水,而且漏的不是一处两处。这样的情况下,课堂就会被打断,挪桌椅、拼座位,有的趁机讲空话,乱作一团。一天,大暴雨,又发生了屋顶大漏,正在上数学课的杨毛雄老师突然停了下来,指挥我们挪坐在淋不着雨的地方,然后镇静地说: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名字叫漏。“漏”是什么东西?大伙儿一下子提起了兴趣,安静听讲起来。因为隔得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个故事的大概:农家夫妇养了一头大胖驴,小偷和老虎起了歹心,一个想卖钱,一个想吃肉。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小偷和老虎同时到达了农家,然后刚好遇到大暴雨,在门外听到农妇跟丈夫在说:“我啥都不怕,最怕就是漏了。”做贼心虚的一人一虎都以为漏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又恰巧阴差阳错地黑灯瞎火撞在一起,都把对方当成了漏,纷纷吓破了胆,都被对方吓跑了。而好玩的结果是,最后杨老师揭晓答案:漏是什么?原来是:农家夫妻怕漏雨。听完故事,大伙都笑得合不拢嘴,早就忘了自己当时正在经历着“漏”的煎熬。小杨老师的母亲杨琴老师是我四下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夫人陆老师后来任教我初中时的地理课,这是一个质朴淳厚的教师之家。
我的小学毕业证书(留有杨毛雄校长印)
不正头。我很是犹豫要不要把这样的一件事写下来,总觉得有那么一点辱师的味。但细细品味后觉得:在当时小孩儿的心里真没有辱师的心理,有的只是那份纯正的童趣。我们5-6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个负责优秀的乡村基层教师。他几乎每学期带我们去后海沙滩上开展一次班集体户外活动,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全班乘轮船上城去探望刚退休的四年级甲班班主任范瑶书老师,顺带游玩了府山公园,在1988年,这样的班集体远游可是一件大事。老师和我同村,我们西溇底的学生上学要路过他家门口,后段就是同路了。因为管理严格,几个稍微调皮些的学生就几多微词,私底下就给老师取了个绰号:歪头(应该不是我们这一届取的,老师的头稍稍有点偏)。有一天,上早学路上,我看到石板路上依着步行方向用粉笔大大地写着几个字:不正头。每个字间隔一、二米,不知情者不会去留意这些零散的字,但我清楚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写给老师看的,像是带有点泄愤。但也许碍于师尊,抑或是孩童的小心眼,他故意把“歪”字拆成了“不正”两字,或许想万一被老师追查也可为自己辩解留一条退路。现在看来,这样的一种自作聪明也真是没有什么了的。
后海泥滩。说是“后海”,其实不是海,是曹娥江,但泥滩确实真的有。从小学校北行两三里,就爬上了一条古海塘,塘外就是曹娥江,此处距入海口不远,江面异常开阔 ,所以乡人一直以“后海”称之。因曹娥江直通杭州湾,来自太平洋的海水伴随着潮汐一天两个来回上下四次侵蚀着江岸,但另一面却是来自曹娥江上游的泥沙因江水流速趋缓而沉积,再加上潮水的顶托,千百年来,江岸泥沙堆积日盛,低潮位时,大片泥滩裸露。塘外江边这一大片咸质泥滩地,又是我们儿时的另一处玩乐天堂。杨琴老师和鲍世越老师都曾经带我们去后海泥滩边多次开展班会活动,骑自行车、放风筝、捉毛蟹、挖海荸荠,追逐、奔跑。最有趣的是大伙拉着手围成圈,齐力在滩涂里上下一致踩踏共振,不一会儿,泥滩变得异常柔韧,半水半泥,赤脚踩在上面,脚感舒适。踩踏的同时,还能把幼年毛蟹从泥滩小孔中逼挤出来,四散爬窜,自然成为我们手中的玩物。玩将一会后,又自然放归,因为带回家也吃不来。这样的泥滩班会往往又与野炊绑定,锅盆、食材都是自带的,而灶基和柴火却遍地都是。泥滩上凌乱堆积着很多乱石,随意搬来几块就搭起了简灶,滩上和塘堤边到处都是茅草,这是最佳的引火料。男生们四散跑开把滩上的矮灌木成捆拔起,生起了火,调皮一点,会去折些别人家的桑树枝来,毕竟成材的树枝比灌木精烧的多。如果是春夏之交,回程路上,大伙定会涌向塘堤内成片的桑树林里采摘桑葚,带回满满的战利品,一顿饕餮盛宴。需要补充的是,在姚家埭村东边几里,就是鲁迅外婆家安桥头村,安桥头的北边是镇塘殿自然村,一个典型的海边聚落,附近还有里赵、外赵,这些都是鲁迅小说《故乡》中描述过的真实地名。迅哥与少年闰土一起月夜守瓜田的处所与我们的玩乐天堂紧挨着,是同一片滩涂。沧海桑田,随着新世纪曹娥江口门大闸的建成,咸潮已被拒之门外,“后海泥滩”已然绝迹,退化成了温润的河滩。建闸拒咸,转淡成陆,我不想评述,我只知道,儿时的玩乐天堂就此没了,不复再生,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我也只能从Google earth中截下了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后海滩涂图片,翻出了相册里拍于1996年农历8月18观潮时的老照片,聊以慰藉。
后海泥滩(2003年8月)
后海一线潮(1996年农历八月十八摄)
抢潮头(1996年农历八月十八摄)
后海滩涂已褪变成静静的河滩(2017.3.27摄)
宋萌萌。学校小操场东侧围墙外的地方叫帅府溇,去那儿必须出校门东走然后穿过一条长巷。外婆曾经告诉我说这里是她的外婆家,因此对帅府溇一直充满了亲切和好奇。溇的对面倒是我常去玩的处所,那是好友宋萌萌家所在。我四下年级从外校转入后,一度与萌萌同桌,由于兴趣相投,所以很聊得来。我自觉自己的历史、地理知识很丰富,但在他那儿却是小巫见大巫。有段时间,我们相约比赛谁识记的国家首都多,竟硬是去死记硬背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首府),利用课间相互出题刁难。为了取胜,两人都专挑生僻的来问对方,什么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等等,很有挑战性。萌萌家门口长着一棵高壮的桑树,那时流行养蚕宝宝,我们就不顾个小攀爬上去摘桑叶,也会在桑树下聊天、侃大山。萌萌没有告诉过我“帅府溇”这个地名的出典,“帅”是谁?这个问题我儿时就留在了心里。外婆也只说是个“元帅”,却不知哪朝哪代。“帅府溇”的谜底一直要到我读大专时在《中国古代史》的课堂上才解开,这是后话。
宋萌萌送我的明信片(1989年小学毕业前)
帅府溇旁宋萌萌家门口(2018.1.27摄)
蛇。为什么事关姚家埭的梦境中时常会出现大量的蛇,这是我始终无法解释的部分。事实是:无论是小学校的校园还是上、下学的田畈路上,儿时的我不时上演着与蛇相遇的故事,特别是在春夏之交。那时没有工业污染,村前屋后的生态很好,清明前后,刚结束冬眠的蛇就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次,与哥哥夜里去秧田里抓泥鳅、黄鳝,不料却捕上来了几条水蛇。成年后的梦境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自己独自一人沿着长溇去上学,一路都是匍匐在田埂上的各种蛇,隔几米就一条,然后我就跳跃式地飞奔,飞奔……醒来后,一阵唏嘘。事实是:有一次,和勇刚他们一起沿着泥渠边的田埂去上学,看见渠中有一条小蛇在流动,好玩的我们捡起一根木棍去拨玩它,蛇钻进了一个洞,我们硬是用木棍往洞里去捅了几下,不料,搅到的是一个蛇窝而且是大窝,估计总数不下两百条的幼蛇,团在一块,一坨一坨地翻滚了出来,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飞也似的逃离。这个场景,算得上是我记忆中最恐吓的一件事了,以至于多年来,还不时在梦境中反复出现。教室的后面是一块菜地,在北边靠围墙处,是一片野林,树高林密,对于我这种胆小的人而言,那里是从来不敢去的雷池。那里更是蛇的天堂,狗乌扑、五步蛇等类毒蛇很多。同学中有位叫谢育林的,是个有奇胆的人,也因为这个,他当时就是大伙的“头”。一次,他独自一人进入密林,不一会,就一手撮着一条大蛇的尾巴将蛇转着圈走了出来。他将蛇在地上一把重摔,然后拔出小刀,当着我们的面,活生生取出蛇胆,一张嘴就吞了下去,一连串的动作,直把我们看得惊呆。这是件确实的事,以至于当时以后对他有了那种莫名的敬畏感。即便后园是蛇的天堂,但小孩们还是抵挡不住密林和草丛的诱惑,一下课就会成群跑向那里,折一段柳枝,盘成花圈戴在头顶,蹲藏起来,见伙伴过来,突然跳将出来吓人。更多时,会分成两队,组织一场“械斗”,玩得不亦乐乎。
蛇的天堂:长溇(1996年摄)
“雷公屎”和“天蛇”。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老同学应慧娟在感忆小学时一放学就会钻进桑树林里摘桑葚吃的场景,不由得想起了姚家埭小学泥操场上的那些风物。雷公屎,即地木耳,顾名思义,是伴随着春雷而生的一种藻类植物。春雷响,万物生,打雷就长雷公屎。往往在一场雷暴雨后,学校两个操场的野草地上,会长出满满一地的地木耳,紧紧密密地挨着长,蔚为壮观。大伙们拎着塑料袋,踩着泥泞,俯身去捡,不一会,就能装满一大袋。然后拎回家,骄傲的向妈妈展示劳动成果。但我好像从来没有食用过一次,可能是害怕有毒吧。在阴暗的泥地中,我还曾碰到过“天蛇”。天蛇,是我们这对一种形似蛇的软体动物的俗称,学名叫“笄蛭涡虫”。那次是因为要去钓鱼,须挖些蚯蚓作饵,搬开石块时突然发现了这种奇异动物。它比蚯蚓细长多了,有两个头,都呈扁平状,与蚯蚓缠绕在一起(外号:蚯蚓杀手)。有意思的是,这种动物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如被切成两半,这两半均可再各自生出失去的另一半,形成两个新的完整个体。同伴的知识面很广,告诉我说这是天蛇,难得一见,并指导我用铲子截断它试试。真的,被断开的两段软体不一会儿就各自游开了,真的很神奇。小学校的大门内侧小天井中有两棵枇杷树,成熟季节,果实挂满枝头,着实诱人。后园中,各班都领有一块菜地,劳动课时,分工合作,施肥、浇水,一片忙碌。最忆的事是,4月和9月,上学路边的大豆、甘蔗分别熟了,我们总会玩儿似的随手摘折些尝尝鲜,还自嘲着这不能算偷,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在做的。
雷公屎(地木耳)
天蛇(笄蛭涡虫)
在19989年6月,那个全国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我从姚家埭小学毕业了,9月,转入马山镇上的初中就读。三年后的1992年8月,我又辗转回到了姚家埭村,就读于帅府溇边的马山中学。姚家埭与我的故事,将拉开新的帷幕。
王庙桥附近水乡景色(1995年摄)